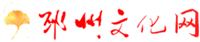本家二叔大我九岁,憨厚老实。
少年时,我又瘦又小,和别的伙伴玩不到一块,最喜欢找二叔玩。
那是八十年代,家家户户几乎都养一头毛驴,平时用毛驴拉磨,秋天来耕地,每逢夏天,他经常背着粪箕子带着我去割草喂驴,那会还没有除草剂,田地的沟边到处是绿油油的青草。
夏天的七八月份很热,口渴难耐时二叔就让我去别人家的地里偷西瓜,然后找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吃,前提是偷来的西瓜我分多半,年幼无知的我倒也开心,总以为占了很大的便宜……
二叔有个家传绝活,喜欢逮黄鼠狼,他用铁丝编了一个长方形的笼子,类似于现在抓老鼠的铁笼子,他把笼子放在门口的柴禾垛子的墙根处,里面再放一块肉,黄鼠狼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每次抓到黄鼠狼他就把皮扒掉,晒干之后留着卖钱。
记得有一次,二叔把扒过皮的黄鼠狼送给了我,我用绳子系上拿到家里放到土锅的炉堂里准备烧着吃,母亲看到之后给扔了,我又捡了回来去找二叔,他拿了一盒火柴带着我来到村西头的沟边,捡了一堆干树枝,把黄鼠狼放在树枝上面烧,不知什么原因,烧熟了之后他一点都不吃,全给我吃了。
回到家里快黑天了,母亲在村里已找我很长时间,看到我的嘴边黑乎乎的,当她知道我吃黄鼠狼之后把我一顿训斥,晚上听我爸说:黄鼠狼有灵性,不能打,更不能吃。
后来,我再也没去找二叔玩过……
到了九十年代初,我上了初中,二叔染上了汹酒的恶习,冬天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有个卖黄豆芽的姑娘天天来我们村,二叔的宅子在村口,他一听到卖豆芽的女孩来了,就披着黄大衣出来买几毛钱的,炒好当酒药,天天如此。刚开始那女孩还用杆秤称豆芽,时间久了,她直接不用秤了,随手抓几把给二叔,以后干脆不要钱了,听大人们说那女孩的年龄和二叔相仿,看上二叔了,最后二叔的家人没同意,后来那个卖豆芽的女孩再也没有出现过……
二叔喝酒越来越频繁,几乎一天三喝,周围村庄的村民无人不知,他正处在说亲的年龄受到了直接影响,有好几个外村的媒婆给二叔说亲,见面后姑娘家人一打听二叔好喝酒,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九十年代,社会正流行国家户口,在那个时期谁家的孩子有正式工作,上门说亲的能踏破门槛。
为了能够成家立业,二叔在十八岁那年去了青岛,军人出身的大爷给他安排了工作,在海军下属的一个医院里做临时工,月月拿着可观的薪水,在那会农村的青壮年几乎没有外出的,能有一份工作哪怕是临时工,说媳妇更容易一些。
九十年代末期,我毕业后也去了青岛,上班的地方离二叔上班的医院很近,步行几分钟就到了,就这样我和二叔又走到了一起。
二叔就像我小时候带着我一样,休班时就带着我逛海边、爬湛山、钓蟹子……有时为了省公园的门票钱,他竟然带着我翻了两座山头,市南区的旅游景点都留下了我俩的足迹,每次出去玩,我们从来不坐公交车,都是步行往返,和二叔在一起很快乐,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
二叔还是很馋酒,天天喝,他经常带着我买几包榨菜坐在马路边的草坪上面喝酒,刚开始他先喝白酒,等到觉得有点上头了,再喝散啤,用他的话说这叫“散打盖顶”。
那几年,老家又有人多次给二叔介绍对象,最后还是因为他好喝酒没能相成。
后来,二叔堕落了,周围的亲朋好友好言相劝也无济于事,他天天沉醉,杯不离手,直到他面部发黄,腹部凸起的时候,去医院检查,结果是晚期酒精肝硬化,没过几年,二叔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以后,每年清明节上坟的时候,看见二叔那孤零零的坟头在祖坟的边远处,上面长满了杂草,都会禁不住一阵心酸:我俩虽然是叔侄关系,还有另外一种感情,因为是他占据了我童年太多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