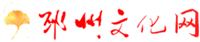|
|
|
一位科学史教师应该站在科学与人文的交汇点。在科学史的第一课,我就告诉学生:“科学史没有答案,但却教会我们怎样思考”。科学史的教学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平铺直叙,而是要把课堂变成充满人文气息、激荡思想启迪的“精神砺炼”。 要引导学生把目光从数学课本里抬起来,沿着文化的桥梁走进数学,这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数学不是枯燥定义的累积,也不是繁琐公式的堆砌,更不是单纯的思维体操,数学有自己的灵魂。在数学与文化相遇的地方,会让他们换一种方式认识数学,从前只能雾里看花的数学世界居然如此绚丽多姿、曼妙精彩! 若期待今日交大之学子,为明日国人之精英,当需交大之老师,敢梦他人所未梦! 教师的激情是点燃学生求知欲的火焰。 再过几年,我的教学岗位会有新人来替代,我的研究成果也会被新人所超越,但那时我会十分欣慰自豪地离开,因为,我为交大播下了拉丁语的火种。 2009年9月摄于布拉格郊外“第谷”天文馆 站在科学与人文的交汇点 2012年3月9日,上海交通大学举行了“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揭牌庆典,仪式简朴,但我的心中却激荡着强烈的使命感:作为一位科学史教师,历史责任要求他必须“站在科学与人文的交汇点”。 19世纪之前,科学还只是“神学的婢女”和“统治者的下人”,甚至怎样称呼这些“研究物质世界知识的从业者”都备感困扰。大约1840年代,有人照着“artist”造出了“scientist”,“科学家”才有了一个“正式”的称谓。20世纪以来,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向世界展示出她那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尤其是当“科技强国”成为“民族发展”主旋律的时候,整个社会都被裹挟在科学技术的“战车”之上。人文社会科学无奈“退避三舍”,“科学”与“人文”两大阵营的对立渐次显现,1930年萨顿(G. Sarton)就表现出了这种忧心,他说:“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就是两种看法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冲突,一方是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这些所谓人文学者,另一方是科学家。由于双方的不宽容和科学正在迅猛地发展这一事实,这种分歧只能加深。”1959年,C.P.斯诺在剑桥大学的著名演讲更是挑明了这一点:“文学知识分子在一极,而在另一极是科学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两极之间是一条充满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是敌意和不喜欢,但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互相对对方存有偏见。他们的态度是如此的不同,以致于即使在情感层面上也找不到共同之处。”萨顿指出了弥合两者裂缝的途径:“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这肯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人们值得为此付出它所需要的代价。”而且,在萨顿看来,“科学史的研究,不仅能看作是智慧和人文主义的来源,而且可以看作是我们良心的校准器:它帮助我们不自鸣得意,不骄傲自大,不急于求成,但却保持着信心和希望,并且为完成我们自己的使命默默地永不停息地工作。” 因此,我的科学史教学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平铺直叙,而要把课堂变成充满人文气息、激荡思想启迪的“精神砺炼”。我会讲牛顿的“光的分解”、“微积分”和“万有引力”,但我一定会展示牛顿如何为求一段双曲线下的面积而计算了55步!我会介绍“血液循环”的发现过程,但我一定启发同学思考为什么维萨留斯发现了心脏的中隔但却没有发现心脏的血液循环?我会赞誉诺贝尔奖的神圣,但我一定让同学知道因人工合成尿素而获得诺奖的哈伯,正是他制造的“芥子气”,使得一战中成千上万名士兵丧失生命。我还会讲黄禹锡,从而使同学们明白从大一开始就应该“诚实做学问”。在科学史的第一课,我告诉学生,“科学史没有答案,但却教会我们怎样思考”。一位学生在学习体会中写道:“从起初抱着新奇的态度上完我的第一堂科学史课,到从那以后认真地听完每一堂科学史课,每一节课都会带给我一次思想的冲击与享受,又留下许久的回味。我想,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课堂,它追溯人类进步的脚印,它研究科学发展的历程,研究科学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使得每一堂课虽身在教室却如同回到历史的时空隧道中与思想大师进行对话;如同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中一样。” 我想,倘若萨顿今日造访交大,读到学生的这段文字,他一定会摘下胸前的“萨顿奖章”,把它挂在“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的铭牌上。 让文化架起沟通数学的桥梁 我不会忘记,十二年前第一次在交大推出“数学史”公选课,却因选课人数达不到20人而没有开成。这种尴尬迫使我去思考:学生需要怎样的数学史?我应该怎样从文化的视角去揭示数学的意义?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中,数学与宗教、文学、艺术、音乐有着怎样的相互影响?这些问题启发我应该引导学生把目光从数学的课本里抬起来,沿着文化的桥梁走进数学,这样他们就会发现,数学不是枯燥定义的累积,也不是繁琐公式的堆砌,更不是单纯的思维体操。数学有自己的灵魂,“它赋予它所发现的真理以生命;它唤起心神,澄清智慧;它给我们的内心思想增添光辉;它涤尽我们有生以来的蒙昧与无知。”([古希腊]普罗克鲁斯) 这样的构想正应合了学校“通识核心课程”的理念,因此,《数学与文化》入选第一批立项的“通识核心课程”。通过阐述不同历史时期数学与文学、艺术、宗教等人文科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分支的内在联系,揭示数学思想演变和数学方法的形成,阐明数学的理性精神和文化魅力,特别阐明数学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不可缺少的重要文化力量。为帮助学生直观的了解数学与文化的相互关系。我会选择放映与数学相关的电影,如《美丽的心灵》、《费马的房间》,或是百老汇音乐剧《费马最后的探戈》;为了给学生创设亲炙大师的机会,我会引导学生阅读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刘徽《九章算术注》、笛卡儿《几何学》、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著名数学原典。在课程结束时,我很想知道学生对这门课感受,就在“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 同学,也许你曾厌恶过枯燥的数字演算,为能在大学里躲掉数学课而暗自庆幸;也许你曾是高中时的解题高手,却为在大学里不再开设数学课而深感失落。但现在大家却在“数学与文化”的课堂上相遇。短短一学期的课程,你看到过:数学,在自然界美丽的花瓣里,在文学家细腻的笔触里,在高耸入云的建筑里,在音乐家动人的旋律里,在引人入胜的电影情节里……。在数学与文化相遇的地方,会让你换一种方式认识数学,也许能帮助你明白从前只能雾里看花的数学世界居然可以如此绚丽多姿、曼妙精彩! Tempus fugit! (拉丁语, Time is flying) 转瞬间,一学期的课程就要结束了。请在这最后一期的论坛里,写下你对《数学与文化》课程切身感受和建议。你的直抒胸臆,你的辛辣点评,都是对完善这门课程的最大“给力”! 一位同学的回复令我十分感怀,他写道: “曾经的我固执地认为数学是枯燥的,在数学的世界里,只有无尽的公式和无尽的演算。曾经的我竟只把数学当作一门考试学科,当作打开大学之门的敲门砖。然而,这一学期,一门课程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原先幼稚的想法,在这门课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数学原来是这么有内涵,这么有深度,其与文化还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联系。这门课便是《数学与文化》。感谢《数学与文化》这门课,带我进入了一个文化的新世界!让数学的理性之美与文化的感性之美结合的那么天衣无缝。感谢纪老师,风趣的授课方式,生动的叙事技巧,还有那精心制作的PPT,带我领略了数学家们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在那一个个晚上,在那一节节《数学与文化》课上,每次都是一次心灵的升华,精神的洗礼。那些数学家们奋斗的经历,他们对于理想的执着,让我为之感动。……毕达哥拉斯曾说过,数是万物之源。数学与文化,让我有了一次寻找‘源头’的机会,一次追问世界的机会。” 教之如此,夫复何求? 在交大播撒拉丁语的火种 2002年4月,我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心”进行学术交流。那次访问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查找一部拉丁语数学著作,即13世纪意大利著名数学家斐波那契的Liber Abaci(《计算之书》,1202)。历史上的丝绸古道,向西方运去了丝绸、茶叶和香料,同时也将中国的科学与文化传入了西方。但是,要真正辨明这段历史,必须给出确凿的证据。在德国朋友的帮助下,虽几经周折,但终于在哥廷根大学图书馆获得了1857年拉丁语版Liber Abaci的全部拷贝。看着厚厚的资料,欣喜与困惑同时涌上了心头:怎么读懂拉丁语呢?未料老师就在身边:我的德国朋友维快(Welf Schnell)博士就精通拉丁语!于是,2002年10月,维快博士专程来到交大,开设了三个月的拉丁语“速成班”,我和几位研究生就成了第一批学员。 拉丁语的“花”首先在研究生论文中结出了“果”,随后自己一系列研究课题都借助拉丁语而获得了惊喜的成果。维快博士回国后,我继续主持拉丁语学习班!说是主持,也就是领着大家一起学。硬是靠着一种信念的支撑而坚持了下来。2006年9月我应邀访问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在进行合作研究的同时,参加了剑桥大学科学史系的Latin therapy。这次剑桥之行,使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把拉丁语作为本科生公选课推向全校。因为,作为一种古典语言,拉丁语是一把打开西方文化宝库的关键钥匙,西方传统的知识领域和研究方法都和拉丁语有着密切关系。当代跨文化研究的主流趋势也要求研究者深入文化内核,方能做出具有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掌握拉丁语可以帮助我们加深理解“西方文化经典”要义,这对于喜爱西方历史、文学、哲学、法学的学生具有特殊意义。医药、农生的学生更可以从专业词汇,拓展到语言的新天地。此外,掌握拉丁语有助于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第二外语的学习,这对于培养新型复合人才,特别是有志于海外交流和发展的同学具有积极的意义。 经过两年的潜心准备,2011年3月,拉丁语选修课向本科生和研究生正式推出。考虑到拉丁语非同一般的难度,在课程介绍的最后一段我特别写道: VENI,VIDI,VICI(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这是Ceasar向我们发出的召唤,让我们一起走进拉丁语课堂,共享拉丁语的独特魅力。当然,在这里你不仅需要十分的惊奇,更需要百倍的勇气和千倍的坚忍,才可获得万分的收获! 交大校园不愧是“藏龙卧虎”之地,第一次开班就有30个同学报名,甚至有德国、南非的留学生和香港交换生,虽然只有18位同学坚持到了最后,但却给了我极大的信心。2012年3月再次开班,这次有45位同学报名,几经调整,现在班上还有29位同学。 有朋友曾问我,花费如此苦功去啃拉丁语,意义何在?价值何为?我多想带着他去见见四百年前的徐光启,1607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其底本就是1574年的拉丁语版本。此前《几何原本》的翻译是“每患作辍,三进三止”,幸运的是利玛窦遇到了徐光启,当徐光启认识到翻译拉丁文《几何原本》的意义后,慨然说到:“吾先正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今此一家已失传,为其学者皆闇中摸索耳。既遇此书,又遇子不骄不吝,欲相指授,岂可畏劳玩日,当吾世而失之?呜呼!吾避难,难自长大;吾迎难,难自消微;必成之。” 教师的激情是点燃学生求知欲的火焰。若期待今日交大学子,为明日国人之精英,当需交大之老师,敢梦他人所未梦! 为交大学子的明天,吃这个苦,值! 在拉丁语的课堂上,同学们还很别扭的朗朗书声,在我听来却十分悦耳。我知道,再过几年我的教学岗位会有新人来替代,我的研究成果也会被新人所超越,但那时我会十分欣慰自豪地离开,因为,我为交大播下了拉丁语的火种。
学者小传 纪志刚,邳州人,运河中学1975年毕业,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奥塞吉学院客座教授,2002年4月-6月德国柏林工业大学中国科学史中心访问教授,2006年8月-12月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访问教授。中国数学会数学史分会第六、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1997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2008年上海交大优秀教师。合著《科学史十五讲》获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教材一等奖、上海市优秀教材二等奖,译著《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获科学文化与科学普及优秀图书“佳作奖”。专著《数学的历史》2011年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2012年受聘为《数学与人文丛书》(菲尔兹将奖得主丘成桐教授主编)特约撰稿人。 为本科生开设课程《科学技术史》(上海市精品课程)、《数学与文化》(校通识核心课程),《数学史》等。为博士研究生开设课程《科学史经典研读》、《数学史研究与方法》,为硕士研究生开设课程《数学史概论》、《科技史文献学》、《拉丁语基础》。 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学史、数学与文化、中外数学交流与传播。主持上海市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 |
站在科学与人文的交汇点(作者:纪志刚)
赞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