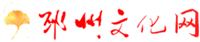动笔写父亲的时候,才发现对他的了解太少。父亲生前极少谈论自己,他的完整生平简历,是从组织部门在他去世时撰写的悼词中得知的。他们那一代人,都是那样谦虚、纯朴,在他们看来,无数战友牺牲了生命,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值得一提,都是应当的,都很普通。记得我曾根据父亲的讲述,写过一篇抗日故事,父亲看到,在那篇文章上批了很多字,给我女儿看,女儿回家来说:“爷爷很生气,要找你说清楚,不要把大家的功劳说成他一个人的。”吓得我几天不敢去见他。但最终,他没找我算账,而我此后再写与他有关的文章,也不敢向他炫耀了。又想到他在九十岁高龄去世时我给他写的挽联:“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赴汤蹈火革命老战士,农业工作科技工作鞠躬尽瘁人民好公朴。”在我看来,父亲就是一位永远的老兵,一位好公仆,这样朴实无华的“盖棺定论”,他应该是认可的。
父亲的生平简历是这样的:1923年2月8日出生在山东省郯城县房庄乡徐蒲坦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三岁失去母亲,上过几天私塾,十来岁就跟人去拉盐卖。1944年8月参加抗日民兵组织,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徐蒲坦村第一个党支部书记,先后又任八乡联防队指导员,郯城六区民兵大队指导员。1947年8月任鲁中南军区滨海军分区郯城独立团二营部干事、书记,1948年任鲁中南十六团第三营分部书记,1949年先后任滨海军分区海防二团政治处书记、华东警备三旅第九团机关支部书记、九九师二九五团二营机炮连副指导员,1952年1月任滕县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纪检干事,1952年12月任徐州人民武装部政工助理,1953年在邳县兵役局短暂工作后,又调到徐州军分区干部科任职。1955年4月任邳县人民武装部政工助理,1958年4月起先后任邳县议堂公社党委组织委员、党委副书记,1960年4月任邳县张楼电灌站站长,1966年2月任邳县李圩农机站书记,1971年1月任邳县病虫测报站站长,1974年12月任邳县堤防管理站站长,1978年8月任邳县植保站站长。1983年4月离休,享受县处级待遇,2009年享受副司局级医疗。
一个人,九十年,从那动荡的年代一步步走来,真是不容易。我已经无法知道父亲小时如何失母受苦,也无从知道父亲在战争年代如何出生入死,只有解放后的工作经历,母亲常常提起,叔叔阿姨们会偶尔讲述,我从小到大,也有所见闻,而有关部门又要编一部在邳州工作的山东籍老干部回忆录,那我就写写这个时期我所知道的父亲吧!
父亲与邳州最早结缘,是在淮海战役中。他所在部队从山东赶来参战,驻扎在运河铁路大桥东头的索家村的一位老农家里。争夺铁路桥的战斗十分惨烈,父亲的战友也多有牺牲。那位老农看着二十岁出头的父亲性格老实、长相和善,见人不笑不说话,特别喜欢,暗地里买来马肉给他吃,天天担心他牺牲在战场上。后来部队打了胜仗一路南下,杳无音讯。解放后,父亲从徐州军分区调来邳州武装部工作,母亲在三联庄当主任,他去看望,竟然又见到那位老农。老人家抱着父亲大哭,说以为父亲牺牲了呢!这是浓得化不开的军民鱼水深情,也是父亲的邳州缘。想来这段经历,父亲应是刻骨铭心。解放后他在邳州生活工作了整整六十年,并且长眠在了这块大地上,对于他来说,邳州,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当然,父亲真正与邳州结缘,并且一生植根邳州,应该缘自母亲。母亲1953年在良壁乡任乡长,1954年初父亲从徐州来邳县检查兵役工作,区武装部长了解到父亲是单身大龄青年,择偶标准一是党员,二是干部,三是贫农,就把完全符合条件的母亲介绍给了他。父亲仪表堂堂帅军官,母亲俊秀干练女干部。两人一见钟情。年中父亲来邳州带兵,与母亲又见一次面,年底母亲就拿着组织介绍信在邳县运河镇领取结婚证,去徐州军分区与父亲完婚。为照顾夫妻两地分居,父亲于第二年4月调来邳州武装部。我于1956年10月出生,可能为了纪念他那段在徐州工作的经历,给我取的名字“徐景洲“中,就含有“徐州“两字。
父亲在邳县人民武装部工作时间近五年,那应该是他一生中最轻松最快乐最顺心的一段时光。没有政治运动烦扰,一心做好预备役民兵和征兵工作,足迹遍达每个村镇。那些年邳县预备役民兵与征兵工作非常出色,为后来成为全国民兵工作先进县打下了坚实基础。父亲那时会吹箫拉京胡,给爱唱的参谋伴奏。花好月圆,歌舞升平,很温馨。想来父亲穿着佩带军衔的军装行走在城乡,很威武很潇洒。父亲一直对部队感情深厚,他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兵。他的一个很大心愿,就是能有一个孩子参军,结果三弟满足了他的愿望。
1958年父亲转业到了地方,在议堂公社担任半年党委组织委员后,被提拔为党委副书记。那段时间正值大跃进高潮期,夸大产量,瞒报收成,是普遍现象,也是“政治正确”的表现。但父亲忠厚老实,有着农民的憨厚、军人的较真、山东人的倔犟,不会说假话办虚事。对包挂的生产队实收实报产量不浮夸,公粮有多少交多少,遇到前来农户家强征公粮的,父亲就出面制止,说人家愿意交就交,不愿意不能强迫。三年困难初期,父亲包挂的生产队,因为队里存留的粮食多,基本没有挨饿的。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因为制止强行收公粮,父亲挨批,打成右倾分子,降职处分,调到张楼公社担任电灌站站长,又一次改变命运的轨迹。到了1960年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甄别干部,撤销了处理父亲的错误决定,但职务,却一时不能变动了。从此,行政级别没变,实职却由科级单位降到股级单位。其间县委要提拔他任公社党委书记,他坚辞不从,唯一要求就是调到县城工作,好照顾家人与自己的身体。而他那原来钢板一样强壮的身体,则在议堂公社工作那段时间埋下许多病根。当时粮食不够吃,许多人患了浮肿病,父亲每天提着沉甸甸的口袋,到各家各户发大豆,因为大豆可以治浮肿病。别人的浮肿病治好了,父亲的浮肿病却严重了,腿肿得油光发亮。父亲看着堆放在眼前的豆子却一粒不吃。这事被李清溪县长发现,特批一批大豆给公社干部,每人每天四两当药吃,终于治好了浮肿病。
从1960年到1966年,父亲在张楼电灌站工作了六年,那六年是全县大力推行旱改水、大种水稻的时期。而张楼公社则是重点推广示范区,电灌站的工作也就至关重要。虽然离县城的家并不远,父亲却极少回家,只是来县城开会时,顺路来家看看。他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跟着公社的丁如光书记跑遍全公社的每一处旱改水的田块,研究如何把大运河的水通过电灌站有效地灌到每一块水稻田里。水是水稻的命脉。为了最大利用水源,有效地分配水源,灌溉季节,电灌站连白加夜抽水灌水,日夜都要有人守候,父亲一天只睡几个小时,操劳在机房里。有电灌站之利的张楼,因而成了全县水稻种植最成功、出产稻米质量最好的地区。当地农民都夸赞:我们有这么好的大米吃,一不能忘了丁书记,二不能忘了徐站长。
文革开始前的1966年2月,父亲被调到李圩农机站任书记。当时正值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全县南北只有两个大型农机站,各负责邳北邳南几个公社的土地耕作,一个站的职工就有五六十人,当时也算是个大单位了。对于父亲来说,也算是提拔重用。父亲到哪儿都没有架子,都要到第一线,像普通的劳动者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拖拉机下乡去耕地,父亲就跟着去掌犁,他坐在拖拉机后面的铁犁上,掌握着犁沟的深浅。那可是个又苦又危险的活。夏日炎炎,冬风凛冽,长时间忍受酷暑严寒的折磨。而夜晚耕地,没有灯火,颠簸摇摆,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栽下犁来。第二年文革风暴更猛,领导干部都要批斗,站里几个领导,唯有父亲无人揪斗,因为他原则性强,从不多吃多占,作风正派,与职工打成一片,吃苦总是在前,实在批不出批斗的理由。不过后来,发生了两件事,让坚持原则的父亲吃了不少苦头。一是造反派将旧轮胎卖了,买了几十双皮靴,想发给每个职工,可是父亲就是不签字,他认为这是公有财产,不能私分,即使因此开会批斗他不关心群众生活,也坚决不从。二是因为有两个职工把拖拉机开到家里保养,又用拖拉机拉自家伐的树,被造反派揪来批斗,说他们既偷拖拉机又偷树,要报公安局批捕。父亲了解情况后,坚决不签字。这下祸惹大了,以包庇坏分子为名,弄到县党校参加学习班好几个月,后来县军代表常团长了解情况后,说徐站长坚持原则,是个好干部,这才从学习班解放出来。
文革后期的1971年,干部落实政策,工作走上正轨,那时父亲因为常年奔波劳累,胃病严重,吃了就吐,盲肠炎拖了半年,再不治就有生命危险了,才住院开刀。县里以照顾父亲身体为名,将他调进县城任邳县病虫测报站站长,一干就是三年。这是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单位,人员大都是大学毕业的科技人员,父亲不以老干部自居,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耻下问,虚心问学,买了大量农村科技书籍来看,很快就由外行变内行,与科技人员打成一片,关心科技人员生活工作,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取得了很多成绩,为文革后农业科技的恢复做出了贡献,得到上级好评。
1974年12月,又被调到邳县堤防管理所任站长,重又忙碌劳累起来。堤防所的业务全都在乡下,他极少呆在县城,整天骑着自行车,带着蓑衣、行李,跑遍全县全部的大小河堤。他走到哪,就住哪吃哪,经常在河堤上的看大堤小屋里过夜,真是沐风栉雨,艰苦备至。不长时间,养好的胃病又犯了,常常疼得冒急汗,饭都吃不下。这时他的自行车上,又多了个药罐子和中药。又因为长时间骑自行车下乡,一天能骑几百里路,患上痔疮,疼痛流血,十分痛苦,光是动手术,就达三次之多。但父亲还是坚持一个人整天骑着自行车,寻访在全县的大小河堤上。这期间,下属堤防所有人给县堤防所每人买了一件雨衣用于乡下出差,别人都拿了,父亲却坚执不要。后来那人把雨衣送到家里,父亲陪他吃了午饭后,还是让他把雨衣带了回去。
又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父亲在1978年,重又调回县病虫测报站任站长,这时,已经改名为邳州植保站,业务范围更大了。父亲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83年4月离休。这期间,父亲为适应新工作新要求,学习更加勤奋,买了许多专业书,做了大量读书笔记,讲起农业科技也能头头是道,植保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成绩斐然,为农业生产做出了很大贡献。父亲在植保站工作时,我经常去他单位玩,父亲就让我给他们刻印简报的蜡纸,帮助印病虫简报。叔叔们也经常去我家,父亲会留他们吃饭,但他们拿来的东西,一律不收。那时我们家六口人住在三四十平米的自建房中,实在太拥挤了,但父亲从不开口要公房。叔叔们多次向局领导反映情况,最终局领导决定分给父亲一套六十平米公房,父亲当即把老房子很便宜卖掉,说一个人不能有两套房。后来平房盖楼,因为某种原因,始终没有办房产证,父亲真可以说是两袖清风而来,不带半根草去了。
说到父亲坚持原则的“迂”是出了名的。他这一生信奉一个信条,就是不能拿公家一分钱好处,到哪儿都如此。记得我小时曾扫货场的炭卖了五分钱,被他发现,硬让我交给了看货场的人。他很多次到公社检查工作,人家摆好了酒席,他就是不参加,自己去食堂打饭吃。有一次被硬拉上桌,他却把自己的酒杯倒卡过来,声言一滴酒不会喝。同桌有个领导大发脾气,几乎要吵起来,但父亲还是滴酒不沾。其实父亲还是喜欢喝酒的,出差回到家,我就得跑到街上去打散酒给他喝。他在公社蹲点时,常常晚上一个人躲在蚊账里偷偷喝上几口。我下放时,曾在赵墩公社彭湖大队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父亲是邳西那一片几个公社工作队的负责人,好几次他来我们大队检查工作,竟然没跟我说一句话。想来是怕工作队领导因此会特殊照顾我。
父亲爱学习也是出了名的。他因为读过几天私垫,在部队一从事与政工和文秘有关的工作。转业到地方后,学习更加刻苦,我小时,就见他有一个大大的木箱子,里面放满了书,有四大名著,有领袖著作,有历史书,政治书。后来,还买来写作书、语法修辞书学习,我考大学时,就拿他买的语法书复习过。他边学还边记笔记,我至今收藏几本他看过的书,空白处密密麻麻都写满了他的心得。他到了晚年,还口述过自己的回忆录呢!我想,写作也应该是他的梦想吧?而我从小爱读书,也多多少少是受他的影响。
离休后的父亲,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坚持读书看报,时刻拿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了一位革命老兵和人民公仆本色,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人生答卷。
2017年6月18日一稿
2017年6月22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