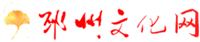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满清政府留给我们的,除了康熙、乾隆外,就是落后和挨打,还有最直观的辫子,从平民百姓到皇帝老儿,一律脑后甩条大辫子,连统兵打仗的队伍,还雅称“辫帅”、“辫子军”呢!
谁亲眼见过清朝真正的辫子?鲁迅先生是这样描写的“上野的樱花开了,望去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头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的、盘成平的,除下制帽,油光可鉴,宛若小姑娘的发髻一样,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无法褒贬鲁迅笔下辫子的丑俊。但我见到过的两位满清遗老留的辫子,总觉得奇怪和不解,当然这也是我们庄最后的两条辫子了。
大约是在刚解放的前后吧,这两条辫子在我们小孩子的眼中就是异类,新鲜、好奇又恐惧,远远的望着不敢靠近。但又离我们家不太远,总会在不经意间猛然看到,心里便“咯噔”的害怕起来,于是乎变着法子远离而去。
这两条辫子,一条是在陈家,大概是老兄弟俩吧?德高望重,一手好木匠活,人缘亦好,名子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统称陈木匠家吧。弟弟身材高大魁梧无辩子,性格温良和善,苍桑的脸堂,唇边蓄一圈浓密的胡须。农闲时提斧带锯,常出没于村里庄外,或在家门口做些木工活计。给人的印象是忠厚而坤士。哥哥看上去苍老的多,躬腰陀背,走路蹒跚,一条短小的花白辫子,无序地盘在脑后,冬天窝在领子里,很难看见;夏天无处可藏,任由脑勺后摇来晃去。我只是偶尔能见到他,或在路上、或在井涯……他的后人令义、令文,都是忠厚老实的庄户人家,令义曾做过四队的会计,忠义敦厚,人缘亦好,得到社员们喜爱;令文名如其人,文质彬彬、聪敏仁厚,颇受村民称道。他们是庄上标准的老户人家,受到人们的尊重;他们一家还有个小得多的陈令荣,我小学同学,聪颖腼腆、白白净净,招人喜欢,同学们都想逗他开玩笑,是个很随和的人。
另一条辫子是在王家。王明奎 ,高个子,准确地说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干瘪老头,脑袋后甩着一条短短的花白辩子,在风里摇曳;若窝起来,就像一把干枯的茅草把,扎眼地悬结脑后,好像从来没有梳理过。肩头总是挂着长杆烟袋,烟包是特大号的,烟嘴不离口,吧嗒吧嗒吸的极响,和谁也不说话,可能也无人愿意和他说话。据说他从年轻时就很霸道。家里穷的叮当响,住在祖上留下的2间破旧东屋里,三十多岁还没有婆浪,后来搓合一个二婚头,带来一个“犊子”,都五六岁了,却说不是他的“种”,一巴掌掴在耳门上,打死了!从此,两口子三天两头打架,他们打架有个特点,不吵不闹,一锅吃饭,一屋睡觉,饿了就吃,吃过再打,无力就歇、见血才停。婆娘也非等闲之辈: 会吸烟,烟袋挂在东屋门鼻上,吸完再挂回去;她力大无比,自已能将一扇磨搬下搬上,刚生过孩子的次日,就怀揣婴孩去井涯挑水;中饭无米之炊时,亲将未成年家狗照墙摔死,烹而食之;有次捉到条蛇,手捏蛇头,甩动蛇身转圈取乐,仍不尽意。复将蛇束于腰间,一手捏蛇头,逼其张口,一手掏烟油灌之取乐……虽两口子死战不休,却陆读生了四个儿子,乳名也有特色,分别叫“脏”、“臭”、“尿”、“屙”。长大后个个膀大腰圆,可惜命运多舛,前途坎坷。“脏”很早就死了,没有妻、更无子。“臭”曾入赘外地,岳父母死后,复归故里。“尿”与一河南逃难女为妻,生一男孩后,女子跑回河南,后来孩子长大也去了河南;这个“尿”不务正业,一贯偷盗抢劫,1953年春“镇反”时,被人民政府抢毙于闫集村南湖。“屙”,臉上有麻子,浑号“麻恶”,刚解放时,曾在我们区队干过,大高个,腰束宽皮带,很威武,后来不知何因不干了,回家务农。据说1958年因生产队冤枉他,在村东湖里上吊自杀了……
王庄最后的辩子,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看到的人更少了。我也是看了一些知情人的回忆彔,才祥知一二的,觉得也有价值,若不整理,岂不被无情的岁月淹灭了……这权作是对村庄史的补充吧——标点符号而已。因为没有标点的记彔是不完整的;就像若没有一滴滴水的汇聚,哪还有什么浩瀚的汪洋大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