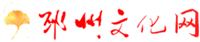在一年的四季中,我怕过暑天。酷暑非但炙人,而且还会给人带来一种莫名的浮躁。白天犹可,忙碌会令人忘却一切。夜晚就不行了。有空调相伴,而斗室仍会令你左右不是。每每当此,我就会不禁心念起儿时的盛夏,在那盛夏之夜,在我家前大运河岸上铺起的大通铺来。
暑天是农闲的时候,太阳一西沉人们就吃了晚饭。饭后除了忙于刷锅洗碗的女人们,男人们是饭碗一推,就头顶着席,腋挟枕头、单被上了河沿。接着就瞄上和自己对味的,一个邻着一个铺起了大通铺。说来也许不被人信,大通铺会铺得很长,每晚是从镇上的沿头直铺到我们村,足足有五里路长,很像一派没有帐篷的连营,看去倒也壮观。
铺好了铺,人们便自觉着安居了,一身的轻松。于是就脱得一丝儿不挂,一猛子扎进了河里,那时的河水既清又甜。热身子浸在碧水里,再抿上一口漱漱嘴,凉浸浸的,甜丝丝的,那种好受,那种过瘾,那种舒心,别说用我那时浅浅的文化水儿形容不出来,就是现在的文化水儿也形容不出来。要说,也只能说个太“恣”了!
泡透了澡,仰面观天躺在大通铺上。此举正应了那人间妙喻:“大大的铺,宽宽的被,河里洗澡地上睡”。静静地望着天宇,天是那么地宽阔,那么地神秘,满天星斗诱惑着人们去憧憬着自己的人生,只有那些时不时拖着闪光的尾巴,贼也似乱窜的流星,才让人省悟着九天之奇。就这样,人们于不知不觉中已做了天之骄子。滑净的肌肤被河风抚摸着,悄悄启开心扉,尽情地承受着大地的恩赐……
大通铺上的人,一边承受着风水天恩,一边构筑着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们用最朴实的语言在进行着梦想和生命的交流。大通铺上的主旋律是高谈阔论。人们在谈天;畅想着牛郎织女会天河那个古老而又美丽的故事;大家在说地,地是无边无涯的,话来也就没有留扯。大事,从斯大林说到杜鲁门;小事,从苏联大花布扯到日本避孕套。扯着扯着就扯到了才发生过的毛人水怪,以及村东头那个乱葬冈中的鬼魅魍魉上去了。像饿死鬼晚上向行人讨豆子吃,白天乱葬冈里那些裸露的骷髅里,都滚动着黄豆粒。还有那个河南籍的烧窑师傅,死后也客居在东乱葬冈里,他活着从事淤泥生涯,死后给了个职称叫“淤泥鬼”。其技能就是抓住人用泥糊。凡是人身上能喘气的地方和带孔的地方,统统用泥糊死……讲得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听得人毛骨悚然,心惊胆颤。吓得妇女小孩不禁拉上单被蒙上了头,大约也就顺势入了梦乡。
其实,河沿大通铺上每晚也不尽是通俗文学。高雅浪漫者亦有之。像贾二哥,人生得俊雅,兴趣也极够品位。他家有一支祖传铜箫,祖上三代皆是品箫能手,于是他从小也就箫不离口,待到他独在大通铺上占一席之地时,他已经很上水平地吹奏起《平沙落雁》了。每天晚上他端坐大通铺上,面南背北,对水当歌,一派伯牙风韵。于是,人们便会从他那指下滑出的音符上,享受竹篁的神韵来,实在是没少给河沿那绿色的夏夜平添几多浪漫来。无独有偶,贾二的洞箫竟然引出彼岸的竹笛来。吹笛者叫安新的后生。竖子虽叫安新,其实是从未安心过,在村里是个一流的玩友,吹打弹拉无所不会,最精熟的是吹笛子。仅一河之隔,这儿的人都很熟知,所以每晚贾二一品箫,他定于彼岸吹笛,一横一竖,一高一低,可谓琴瑟友之。曾几回吹得大通铺上的人们心动神摇,竞激情两岸,对水当歌了起来:
什么人领导共产党?
什么人带大军渡过长江?
什么人往前方运粮草?
什么人在后方喜洋洋?
哪么依呀嗨!
彼岸在唱着问。调子是《小放牛》,这儿的人熟得很,于是便齐唱答:
毛主席领导共产党,
朱总司令带大军渡过长江
老百姓往前方运粮草,
儿童们在后方喜洋洋。
哪么依呀嗨!
没等唱完,来自两岸那舒心畅怀的笑,已飘落在大运河的浪花上了。有一回我的近邻,把儿匠刘大叔可沉不住气了。他是远近闻名的喇叭匠子,人一唱他便心动手痒,于是就祖孙几代一齐抄家伙,兴致盎然地吹起了(馏金番调)、《落鸿)、(百鸟朝风),博得两岸大通铺上欢声笑语一浪高过一浪,真可谓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农家乐矣!
当然,村子里也有不入大通铺的,一是自视清高者,持着遗世独立的风骨而独处;再就是新婚燕尔的小夫妻,他们羞于人群是可想见得到的,他们只好远离大通铺.将洞房里的卿卿我我移情到河沿这个幕天席地上.那独立的话语,特殊的心境,汇成一股圣水流入爱的芳圃,将酿成人生的精华。
河沿大通铺是欢乐的、祥和的,但有时也会上演恐怖与惊险。如洪水满槽时,说不定河里就会淌来个“不速之客”,早上醒来方惊呼,原来大家曾与死尸共度良宵,怎不后怕。还有那蛇,有时清兴一来,也会不请而至与大通铺上的人同床共枕,只是它们自恃没毒罢了。当然,这些惊险画面都是极偶然的事。可恼的还是那个叫庚琛的小子。竖子好梦魇,冬天梦魔常常拿其父的鞋帽当尿罐使。在河沿大通铺上梦魇就换了花样,隔三差五地突然梦中惊醒,然后一惊一乍地窜入河里,游上个三五圈再回来睡觉。亏得小子水性好,否则,准有去无回。再就是娄家的老二有夜游症,睡梦中醒来要么爬屋,要么爬树,要么徒步远游。有一次竟跑出去十多里,梦醒时天已大亮,裸体难归,只有顺着河沿趟着回来。此事一直被人笑到娄二入土。当然,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恐怕还是那夜来的不测风云了。那还是没有很像样的天气预报的年代,往往晚上皓月当空,繁星满天,而半夜人们睡得正浓时,倏地闪电雷鸣,狂风大作,此时从梦中惊醒的大通铺上的男女老幼,会惊鸟出林似的慌不择路乱跑乱窜,慌乱中丢苫子忘席,抛枕头,弃单被,甚或忘抱孩子者也有之。记得一次我就丢了一条花被单,疼得我娘直嘟囔到我娶妻生子也未罢休。亏得现在河沿大通铺已绝迹了,要不我一定会丢掉我的猛男衬衣,甚或心爱的诺基亚手机。即使丢了我想我也不会怎么遗憾,遗憾的是我那嘟囔我的母亲已经西赴瑶池,再也不会啷囔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