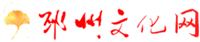闲暇的时候浏览网站,发现母校东南大学搞了个征文,主题是“恢复高考四十年暨改革开放四十年”,邀请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这三级校友把自己四十年前参加高考的故事、上学的故事写下来。
母校的网站上,校友们热情高涨,纷纷撰稿,忆往事、看今朝、谈感悟。于是,我也不甘寂寞,写一写自己参加高考的那点事儿。
一
我的高考故事,要从一九七六年讲起。
一九七六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地动山摇、悲喜交加的一年。
那一年,天降陨石,最重达1770千克的陨石成为“世界陨石之最”;
那一年,地震频发,在唐山7.8级大地震中,24万人瞬间亡殁;
那一年,国柱倾塌,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全国人民悲痛不已又忧心忡忡……
经历了太多的苦痛之后,那一年的十月,“四人帮”被粉碎,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旋即,一首歌传遍大江南北:
“美酒飘香歌声飞,
朋友啊请你干一杯,
胜利的十月永难忘,
杯中洒满幸福泪。”
这首歌,应该算是中国告别一个时代、开启另一个时代的序曲。
就我个人而言,那一年,也有一件大事值得记录:那一年,我高中毕业,十六岁。
二
在那个年代,高中毕业就意味着学业结束,因为那时没有高考,高考已经在“文革”开始那年就中止了。那时,学生们的去处只有一个——“上山下乡”,到山区去,到乡村去,参加农业生产。他们有个专门称呼——“知识青年”,简称“知青”。“知青”又分两类,城市户口去乡下的叫“下乡知青”,农村户口回乡下的叫“回乡知青”。同样都是在农村当地球修理工,但称呼却不同。仅从这些称呼上就可以看出,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是何等森严啊!
高考中止了,高校还要招生。高校的生源,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中选拔,由各级组织推荐产生。选拔的标准主要看政治表现,文化在其次,当然也有人脉、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潜因素。所以,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又叫“工农兵大学生”。导致后来,社会上的一些人就有点倨傲地说:
“我是正规考上的大学生,他是推荐上的工农兵大学生!”
我对他们的倨傲并不赞同。这就相当于当年把知青分为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一样,人为地划分这种无聊的等级有多少意义?
英雄不问出处,主要看气质。
三
话说远了,回到正题,继续说我的高考故事。那一年,尽管“四人帮”的倒台让人无比振奋,尽管“美酒飘香歌声飞”唱得人心潮澎湃,然而我们这些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的“知识青年”们,还是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我学会了许多技能。虽然只有十六七岁的年纪,但是耩麦割稻种棉花、除草施肥打农药,我都做过。农活的苦和累自不必说,有时候还有一定危险。记得是在一九七七年的盛夏,我与小组里的十几位青年人一起为棉花田打农药,别的人都没事,我却感到头晕脑胀,恶心欲吐。送到医院后医生诊断说,不是中暑,而是农药中毒,好在是轻度的,如果那天再闷热一些,如果农药的浓度再大些,就麻烦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我筋骨,饿我体肤,从七六年毕业,到七七年深秋。
深秋十月,从北京传来一条爆炸性消息:中央决定,立即恢复中止了十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
这消息让举国沸腾,让无数的青年人欢欣鼓舞。如果说粉碎“四人帮”是那个年代的第一声十月春雷,那么恢复高考不啻于第二声十月春雷。希望的天窗在关闭了那么久之后,终于打开了!
四
毫不犹豫地就报了名,因为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报名之后心里却打起了鼓:人太多了!从七七年毕业的应届生到六十年代毕业的“老三届”,工农兵学商各个行业的十多届高中毕业生基本上都来报名,大家都希望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据说那年,江苏省招生人数也就二万人,但报考人数就达三十多万。由于人数太多,省里专门设置了预考,目的是通过预考刷下来一批,再进行统考。
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学习成绩一向不错,用现在的话说,可以“碾压”绝大多数同学。然而,当我丢下手中的锄头,重新拿起笔来准备参加高考的时候,却发现眼前一片茫然。首先,时间太紧。从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到参加十一月份的预考,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根本来不及系统复习;其次,对手太强。尤其是“老三届”,他们毕业于“文革”开始前后,基础扎实,学业上受“文革”的冲击不大,许多人还从事教师等职业,对我们来说,“老三届”就是个神一样的存在;第三,自己太弱。我们那届高中生,只在高一学过一段时间文化知识,到高二,数学讲“优选法”,物理讲“三机一泵”,化学讲“土壤分析”,什么指数对数极坐标,什么焦耳瓦特开尔文,什么有机无机化学键,对于我们这届“知识青年”来说,一律陌生。
五
为了支持我考试,父亲拖着行动不便的腿四处奔波,今天一本明天一本地为我寻找复习资料。找来的资料五花八门,有参考书,有习题集,有五十年代用繁体字铅印的,也有最近用不太工整的字体油印的。我不知道这些资料是父亲跑了多少路,找了多少朋友,说了多少好话才借来的,但是我分明能够感受到父亲那颗期待的心。拿到这些资料,我就像深山里的练功者得到武林秘籍一样,如饥似渴地投入其中。
然而,毕竟是生平第一次参加这种攸关命运的考试,随着预考时间的越来越近,心里也变得越来越慌。临考前几天与父亲交流的时候,我不无担心地说:
“爸,心里没有一点底,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啊?”
父亲鼓励我说:
“别考虑那么多,万一考上了呢?”
就这样,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硬着头皮走进预考考场。考场外的大门上拉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横幅,望着横幅我心里想,我大约只有第二种准备吧?然而,十多天后公布的考试结果却出乎意料,父亲所说的那个“万一”应验了,我竟然通过了预考!
预考的顺利通过让我信心大增,心想看来高考也不是太难。后来听说,那次预考,从全省三十多万考生中一下子刷下去了二十多万人。所幸,我不在那二十万人里面。
三十晋十之后,紧接着就是十晋二(数字后面都省略一个“万”字),在十二月的寒风中,统考如期举行。这一次,轮到我所说的那个“万一”应验了:黄金榜上,名落孙山。
仿佛就是一场梦,懵懵懂懂地去参加预考,懵懵懂懂地就通过了;豪情万丈地去参加统考,却灰头土脸地被淘汰了。
六
高考失利让我的自信心受到了沉重打击。虽然我在本届同学里成绩还算不错,但是与十几届同学一起竞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真的能行吗?
一九七八年新年的钟声刚落,那些考上的同学就领到了录取通知书,兴高采烈地开始准备入学的行装。对他们来说,崭新的大学生活就要开始,毕业之后他们就可能成为科学家、工程师、国家干部,等待他们的,是美好而光明的未来。然而,这一切都与我无缘。那段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搭的一间防震棚里,足不出户,黯然神伤。既为辜负了父母的期望而感到内疚,又为自己的前程而忧虑和彷徨。同时,也在心里总结失败的原因:除了基础不扎实,还在于复习的方法不科学,盲人骑瞎马,东一榔头西一棒,自乱方寸。
对于我的失利,父亲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他只是鼓励我不要灰心,准备参加七八年的高考。七八年的高考改在夏天进行,只有五个月了。父亲告诉我,他已经和我高中母校的数学老师黄佑文联系好了,让我开学就回母校,到七八年应届毕业班里去插班复读。
七
春节刚过,我就背起了书包,回到了阔别一年半的学校重新读书。数学的黄佑文老师、化学的陈正萍老师是我上高中时的任课老师,他们很热情,我遇到了什么难题,随时都可以找他们请教。学了一个多月之后我就发现,我一点也不比这些应届生差,每次测验,我的成绩在班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同学们学习上有了什么问题,都爱找我寻求帮助,甚至有一位也准备参加高考的年轻老师,主动要求和我结对学习,他辅导我物理,我辅导他化学。
离高考还有三个月的时候,县里在另一所中学为往届生专门开办补习班,黄佑文老师又把我推荐到那个补习班去参加学习。补习班的情况就好多了,不但讲课按照《高考大纲》的要求系统全面,而且复习资料也更丰富。在那里,我的成绩仍然名列前茅,去年统考中受到打击的自信心,慢慢找了回来。
那段时间,我也付出了超常的努力。补习班距我家有近二十里路,我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往返奔波。一大早就从家中出发,整个白天就在补习班温习功课,晚上回家后,吃过晚饭就在防震棚里看书和做题,常常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两三点钟。经常是母亲半夜起来,看到我还在灯下苦读,就说:
“培义,别看了,早点歇着吧!”
我嘴里答应着,眼睛仍然没有离开课本。也有时候看着看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照常骑着自行车去补习班上课。
八
复读和补习的四个多月飞快地就过去了。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日,我和全国六百多万考生一起,走向考场。考场外的大门上,“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横幅依然醒目,只是这次,我志在必得。
考试过程基本顺利。只不过满意之中也夹杂着遗憾,数学的一道题,在复习的时候我曾经遇到过,考试的时候感觉会做就先放到一边,没想到最后时间太紧,来不及做了;化学的一道题,明明已经生成了白色氯化银沉淀而反应结束,我却脑子一抽,又画蛇添足地搞了个离子反应。仅此两题,少考十来分。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直到八月份的一天,黄佑文老师骑着自行车汗流浃背地来到我家。他刚参加完市里的阅卷和统分工作,从内部渠道提前知道了我的分数:386.5分。
虽然还不知道这个分数比体检线高多少,但是我知道,大学的校门已经向我敞开,坎坷之后,命运之神终于露出了微笑。
我们的故事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在人生的旅程中,四十年应该算一段很长的岁月,长的足以让人忘却很多故事。但是四十年前的高考,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我们个人,都是永远不会尘封的珍存。对于国家,它吹响了改革开放的预备号角,它集结了改革开放的急需人才;而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我们奋发过,努力过,我们的命运也因此生发了轨变。所以今天,在回首那段往事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也曾拥有过蓬勃绽放的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