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初期,时兴穿解放军绿军装。真军装少,只得把白布染绿到缝纫铺缝制。县城洗染店只染蓝、黑、红三色,徐州染布厂就来县里揽活计,说是支持群众革命要求。我刚十岁,也缠着母亲要军装穿。母亲被缠得没法,只好买来代用布(包装货物用的粗布,不要布票),给我们弟兄几个每人染制了一身绿军装。
母亲是洗染店经理,对徐州同行来抢生意,很不满,说那染的布,哪里是草绿色,简直就是“狗屎黄”,不像解放军绿军装,更像国民党军“黄狗子”军服。她打开柳条箱,拿出一套真正的解放军军装让我们开眼界。这是父亲从部队转业后,当预备役军官发的一套军服,还有金灿灿的肩牌和红艳艳领章,大盖帽,宽宽的斜挎腰武装带,捷克式军用大皮鞋,是完整的一套苏联制式军官服。我们惊喜得大呼小叫,非穿不可。母亲说这衣服太大了,要穿只能穿上衣,也只能穿一天。这套军服,父亲非常珍视,从不示人。
冬日早晨,我如愿以偿穿上父亲的军官服,和母亲一起去粮店买粮。我大摇大摆、耀武扬威走在街上,很多人朝我投来艳羡而又惊奇的目光。经过人民剧场旁高高的宣传台,我特意爬上去,学电影里解放军指挥员模样,叉腰挺胸、威风凛凛而立。有人大声说:“这孩子穿得像袍子,真滑稽!”我知这不是好话,羞得忙从台上跳下来,低着头,朝母亲追去。
买回粮食,母亲给我掸一掸身上的灰,说可以出去玩一会,切记不要把衣服弄脏了。我巴不得这一声,撒腿就跑。
立刻有左邻右舍小孩紧紧簇拥我,大街上的羞辱忘到九霄云外,神气十足地把他们带到鱼塘边朝阳避风的大土坑里,把书里看到的战斗故事当作父亲的英雄事迹,添油加醋讲给他们听。他们听得入迷,不时摸摸我的军服,好像父亲当年就是穿着这身军装打日本鬼子,也好像我就是打过日本鬼子的八路军。
有人发现一条小鱼冻在冰层下,像发现敌情,兴奋大叫。我穿军装,理所当然冲锋在前。一手抓草棵子,一手拿石块破冰抓鱼。冰层砸碎之时,草也被连根拔起,上身栽进冰冷刺骨水里。大家把我拉上来,崭新军官服弄湿弄脏,万分沮丧,自己反像打败仗垂头丧气的兵。回到家里,母亲倒没打我,只是把衣服擦了又擦,放回箱子里,我也再不敢提穿军装的事了。
七十年代初,绿军装依然最时髦。我上了初中,个儿长高了,母亲拿出父亲的军服让我穿。我欣喜若狂,弟弟也坚决要穿,争执结果是每人穿一个月。再后来他穿军装,我穿父亲军用大皮鞋。穿大皮鞋走路咔咔响,特精神。伴我上完中学,插队落户,直到大学毕业,穿得帮裂底掉,才恋恋舍弃。但心里还是不满足,总觉得军用大皮鞋不如那身军官服来得风光。
上大学军训时,看到好多同学都找来军装穿,我便回家向弟弟要来了那件军官服。裤子还是半新,上衣却褪成白色,许多地方磨成布丝丝,背面用伤湿解痛膏补着。洗得发白的旧式军官服,在没有恢复军衔制的时代,最受青睐,有历史沧桑感,有革命荣誉感。匍匐爬行训练时,上衣吱吱作响。一趟下来,磨开好几个大口子。一天下来,已是遍体鳞伤,无法再补再穿。唉!没想到这套军服,始穿者我,终结者我。不久,入伍的三弟送给我一套新军装,我穿了好几年,还特意照了一张军装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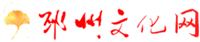
评论列表(1条)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