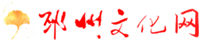六、七十年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由自然灾害、计划经济衍生出一个怪胎,那就是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票、证、券,城市居民几乎家家都有一个抽屉专门放置名目繁多的票、证、券,有粮证、煤球证、工业券、专用券、备用券,要说出“票”的名字足以让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瞠目结舌的了,有粮票、煤票、布票、油票、糖票、猪肉票、香烟票、肥皂票、火柴票、煤油票、线票、豆腐票、冬储白菜票……,以上票证都是按人口定量发放的。
粮票分为米票、面票、粗粮票、细粮票、地方粮票、全国粮票……。如果你要跨省出差没有全国粮票绝对是寸步难行的。
票证留给四十五岁以上人的记忆是苦涩的,然而,票证留给我刻骨铭心的记忆却不是物资限量带来的窘迫,因为那时我只有十几岁。
那是一九六七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家临街的大门被人轻轻叩响,我和妹妹同时向门口跑去,妹妹抢先把门打开但立即“啊”的叫了一声,“砰”的把门阖上,我走上前去,趴在门缝一看究竟,只见一个四十多岁的、穿着黑棉袄的农村汉子低着头站在门口。我马上夸大其词的向爸爸“告状”:“爸爸,她把人家要饭的头碰破了!”
也许是怕要饭的耍赖,也许是怕门口围观的人太多,爸爸把那要饭的让进了家门并倒了一杯开水给他,那人坐在凳子上仍然低着头,嘴里不断的低声说:“我不是要饭的,我不是要饭的。”
虽然爸爸和那人年龄差不多,爸爸还是很有礼貌的叫那人大哥:“大哥,你想干嘛呢?”
那人喝了一口水,说:“是这样的,闺女有病,乡下卫生院看不了,我带她到市立医院查出了肝病,大夫交代要多吃糖,城里什么都 要票,我上那弄去,可难为死我了!”
爸爸想都没想立刻招呼妈妈一起到屋里找糖票,不一会儿,爸爸把一叠糖票和一些零粮票递到那人手里,那人哈腰点头、千恩万谢的走了。
我和妹妹交换了一下眼色,心里明白:这一季度甚至半年别想吃糖了。
慢慢的家里所有人把这件事忘却了。
次年的秋天,我们家临街的大门又被人轻轻叩响了,开门一看,原来是那农村汉子扛着一个大口袋出现在门口。
进得门来,那人把口袋里的东西倒出来,原来是精心挑选的红皮红芋,他说:“山地红芋,又甜又面好吃哩,俺乡下也拿不出啥好东西来。”爸爸赶快问:“闺女怎么样了?”那人淡淡的说:“死了,那是看不好的病,欠下了很多钱还是没看好。”大家唏嘘了好半天,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几斤白糖是救不了肝癌病人的命的。
那人不愿在我家吃饭,执意要走,爸妈也没留他,只是临走时送给他几件旧衣服。
从那以后每年秋天他都要送一口袋红皮红芋,像这样亲戚般的交往持续了好多年,直到城区旧房改造,我们家迁到另外一个居民小区才失去联系。
如今,年迈的父母经常念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算起来他也有八十多岁了,大概死了”,“用什么办法能联系上他呢”……
这就是票证留下的记忆,我每次回想起这件事都感慨良多,是因为父母的宽厚呢,还是因为农村人的淳朴呢,还是因为物资匮乏给人们带来的无奈呢,我也说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