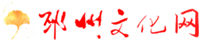都把“知青”文学称为“伤痕文学”,都把“知青”经历叫做“苦难岁月”,我还真不这么认为。正是那五年的知青经历教会了我勤俭节约,正是那五年的知青经历锤炼了我吃苦耐劳,正是那五年的知青经历锻打了我的性格。
因为我和妹妹在同一所学校读书,所以随着全国一千八百万知青被六十年代末的“上山下乡”大潮一起冲到了江苏邳州合沟公社长集大队第三生产队。
我下放的地方一个“穷”字就全包括了,插队落户的第一天晚上,不满十七岁的妹妹满墙摸电灯的拉线开关,几把没摸着就失声痛哭起来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地方能用上带玻璃罩子的煤油灯的就算是好户了。
当时的生产队长在村里权威很大,所谓:“村东头一跺脚,村西头直晃悠。”他的思维可以左右村里大多数人的思维,同样是“知青”,这个生产队队长认为你是犯了错来的,那你就得好好改造;那个生产队队长认为你是派来的劳动力,你就得好好干活。至于我,说出来你别笑,我是插队插巧了,队长和我一个姓,俺这个知青小组都跟我沾了光,嘿嘿!你就看跟俺一个姓的队长在生产队大会上,左手叉着腰,右手挥动着,可个嗓子咋呼:“老少爷们儿们,姊妹娘们儿们!人家爹娘把孩子从几百里以外送到这里,难道咱四百多户贫下中农养活不了几个下放学生吗?我宣布,以后副业组木匠的砍渣、劈柴都归下放学生烧!”多高的待遇啊!别队知青只能烧稻草。烧稻草做饭你知道吗!如果你不会烧锅,满灶膛堆满了草灰,熏得你鼻涕眼泪一起淌,还做不成一顿饭。
我们知青小组在我的带领下,秉承:不参与家族姓氏斗争,生产队长叫干啥就干啥的原则,与贫下中农相处得还算和睦。
清明过后就是谷雨,正是种春稻的季节,我和妹妹整天泡在水田里,我挑稻秧,妹妹插秧。你看看妹妹的打扮:光着脚,卷着腿,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黑亮黑亮的脸膛,和当地农村小大姐别无二致,腰间还扎着一条长头巾。
腰间扎着头巾的目的有三:这一,把辫子扎进头巾弯腰时辫子不至于掉进泥里;这二,头巾扎腰不会腰疼;这三,头巾扎腰弯腰时不会露出后背的皮肤。那时候的女孩子绝对不会穿露脐装和露被装的呦!
我插队的地方方圆几十里有一组约定俗成的称谓:三十岁以上的女人叫“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三十岁以下的女人叫“当代花木兰”,简称“花木兰”;三十岁以下的男人叫“基干民兵连”简称“基干连”;三十岁以上的男人叫“壮劳动力”,简称“劳力”。
每天清晨,生产队长站在村口高台上,会用一声长长的“呃”字叫醒每一个人的耳朵,把当天的农活分配得井井有条:“呃———劳力,稻田整地;妇联,秧板田拔秧子;基干连,挑稻秧子;花木兰,稻地插秧;抓紧走了———!”
大田里,几个“劳力”用鞭子驱赶着水牛把一块块水田耙平,然后由“花木兰”把稻秧插下去。艳阳下,和熙的春风吹拂着每一个人,大家整地的整地,拔秧的拔秧,挑秧的挑秧,插秧的插秧,偶尔传来“花木兰”爽朗的笑声,好一幅《稻田春忙图》。
有点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水稻田里遇到泥鳅、鳝鱼、癞蛤蟆和小水蛇是常有的事。
在忙碌而平和的气氛中,忽然有人说:“珊子,给你这个!”(妹妹叫佩珊,老乡们亲切的叫她珊子。)大家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叫新华的“劳力”用铁锨挑着一条半死不活的水蛇往这边一扔,虽然是虚晃一下水蛇撇到了旁边,但是一块湿漉漉、冰凉凉的泥饼不偏不斜掉进妹妹的衣领里,面对这猝不及防的情况,妹妹“哎哟”一声跌坐在水稻田里,面色苍白,直愣愣的说不出话来,看到这情况,我头上的火苗一下冒了起来,窜上去要揍那个冒失鬼,好不容易被大伙劝住,新华面对大家的训斥,讪讪的过来赔礼,嘴里念叨着:“真无趣,真无趣。”我也只好扶着妹妹回家换衣服。
接下来的事可把我给难为死了,妹妹连续几天发着高烧,不吃不喝,精神非常萎靡,吃了退烧药也无济于事,我可怎么办啊?我才十九岁啊!乡亲们纷纷前来探望,都说是“魂”吓掉了。
于是,生产队长派他母亲和另外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娘来给妹妹叫魂。两位老人家从生产队仓库挖来一瓢黄豆,让我找来妹妹吓掉魂当天穿的上衣,为了保证叫魂质量还神秘兮兮的把我赶出房间。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屋外徘徊,不知道两位老人家怎么折腾妹妹的呢,实在忍不住就从窗户缝向里望去,只见得:生产队长的母亲端着瓢,每叫一声往地上扔一粒黄豆,另一位老大娘拎着妹妹上衣的领口在屋里转悠,妹妹坐在床沿上。队长的母亲叫一声:“珊子回来吧!”另一位老大娘回答:“回来喽!”这样的过程也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屋里忽然传来妹妹的笑声!我赶紧跑到屋里,妹妹已经笑弯了腰,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件上衣竟歪歪斜斜立在地上,据两位老人家说:珊子回来了。
不知是被两位老人家逗乐了呢,还是什么心理暗示,妹妹竟一天天好了起来,活泼的珊子真的回来了!
事情已过去了好多年,如今每当看到小孩子受到惊吓,家长抚摸着孩子的头唠叨着:“孩子别怕,孩子别怕!”的时候,我总是一脸严肃的说:“管用!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