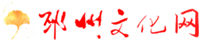大舅家的大女儿我的大表姐,下放的年代来到了徐州,对大城市的眷恋吧,没有返回就找了周姓的人家作嫁了。住在王陵路的培正巷。姐夫是个弥勒佛般的大胖子,能吃能喝,体重足有二百斤,走起路来浑身的膘油凉粉样的发颤,记得他家里有个带把手的石头疙瘩,后来知道那叫“石锁”由锻炼臂力用的,姐夫说他能连续举多少下,可是我去他家几回也没见到他真正的举起过石锁。
七十年代,城里有门亲戚那是很荣耀的,在同学间是可以跩一跩的,所以寒暑假我都要到徐州过上一段时日,回去向同学炫耀我的所见所闻,讲讲外面的精彩,毕竟咱见过市面。培正巷是条老街巷,在奎河的边上,社会不断发展,城市动迁也很厉害,可是这条街巷这么多年,仍然没有改变当年的模样,几栋红房子现在还孤零零的立在那里。那时的奎河臭气熏天,沿河的厂矿企业都把污水向奎河排放,黑黑的污水流淌着无休无止,就像老舍笔下的龙须沟。
表姐家的房子是很紧张的,一间屋子隔开,里面能摆放两张床,外间就是吃饭的地方了。暑假在表姐家还算好过,晚上拿着席卷夹个毛巾被,不觉就天明了。寒假冷了,那就是一夜抵千年般的难熬,在表姐家争床夺铺就显紧张局促了。家里住不下,我们就去外面想办法。那时武打片方兴未艾,表哥就骑着大架自行车带我满城跑看电影,从云龙山到庆云桥,从东站到段庄圆盘,从云龙电影院到中山堂,从鼓楼立体电影院到徐钢俱乐部,到处都留下我们快乐的身影,所以我对徐州市内的道路很熟。玩累了困了,我们就到东站的茶社借宿。
说是茶社并非现在商谈品茗的优雅去处,那是方便旅客等车的临时场所,一个大通间可以摆放三十多张白帆布綳起的躺椅,中间燃起一个锥形的憋气烟煤炉子,一把铁皮卷制的炊壶,在铁板上喘着粗气,可随时为客人提供开水。一个值班的中年男人,像个监考老师一样来回巡视,因为等着赶火车的旅客时间不是一个点,值班的人就根据旅客提供的时间,在脚边用粉笔写下再画个圆圈,不时地看看东墙上悬挂的烟台木钟,到了你约定的点,他会准时叫醒你保证不会耽误车次和时间。茶社就像是一个没有水的大澡堂子,旅客在门口吊挂的旧棉被的开合间来来走走,出出进进,茶社里的空气浑浊憋闷五味杂陈,有用搪瓷茶缸泡煎饼吃的,有解放鞋混合胶皮的臭味,有老烟枪抽生烟丝发出呛人的味道,呼噜声此起彼伏,间或还有人在睡梦中挤出一个响屁来。
茶社早已不复存在了,蓝天还是那片蓝天,只是随着城市的扩容,现在变成了寸土寸金繁荣的都市商圈了。每每路过此地,我便会驻足下来,望望楼下去回味我曾经借宿茶社的点滴,那是我成长的经历,那是我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