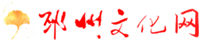20世纪70年代,南京博物院与邳州文化馆在邳州市燕子埠乡尤村清理了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彭城相行长史事、吕守长缪宇墓,该墓除发现了迄今所见最早的墓志铭外,尤以墓门内堆土中清理出的一尊高7厘米、重560克的鎏金铜坐像(图一)颇为引人注目。铜坐像左手置于膝盖上,右手上扬,掌心向外,形似作施无畏印的佛造像,故有邳州文物工作者在预先判定了其佛造像的前提下,给予了该鎏金铜坐像以如下解说:“造像呈屈膝跪坐状,右手拇指分开,四指并拢向上举过耳,掌心向前,示无畏,长袖垂于腕下;左手轻轻放在右膝(按:实应为左膝)上。面阔耳硕,头发向后梳成一髻,上横插一簪,露出前额,面部静穆,双目圆亮;两肩宽长翘起,鼻圆凸,嘴巴抿起;下巴圆阔,胡须髯髯,梳成古月,整个面部神态严肃而又不乏慈善心态。鎏金铜佛身着长袍裟衣,袍上饰鎏金云气纹,襟边、袖口及后腰部饰鎏金带,长袍遮住双膝,后背露出双足,足底肉结高起……(鎏金铜坐像)衣以锦彩,右手示无畏,左手触地,高肉结,眉毛上翘,嘴角古月,都显示佛教造像的特征。”并进一步“由此推断,造像应为东汉时代铸造,缪宇当时应是佛教的信徒无疑。”[1]图一缪宇墓出土的鎏金铜佛造像
但在笔者看来,该鎏金铜坐像的形态既与上述文字描述存在着较大出入,且多见与佛教造像明显不合的体态特征,今试为辨析如次。
佛陀作施无畏印,意谓能解除众生疾苦,其姿势例为:右手曲臂平伸,手腕略与地面平行,手掌向前(即向外),手指向上。至于手掌所在高度的相对位置,大凡作善跏趺坐(即倚坐)者普遍较低,约在胸腹之际;作结跏趺坐者,手掌所在位置虽普遍较高,但也只在胸际。缪宇墓出土此铜坐像右手虽亦掌心向外,但曲臂作上举状,前臂不与地面平行,且手掌高至耳际。就其手势而言,与佛陀形象常见的施无畏印显然去之甚远。另一方面,即便是施无畏印,在中国佛造像上的出现,也是比较晚的,约至五世纪末、六世纪初以来始较多见到,而此前所见凡能明确认定为坐佛形象者,其手势几乎无一例外地施作禅定印。
其次,现今所见与缪字墓纪年相近的中国本土佛陀造型,如早至公元3世纪的北方供养金铜佛,以及南方东吴西晋时期出产青瓷器和青铜器上的饰佛,其头顶心部位皆设置呈球状的高肉髻,与印度早期佛造像肉髻形制完全一致,故可证此种球状高肉髻实为佛教初传中国之际、本土造像的典型特征之一。晋末南朝初,伴随着民众对高僧道安于襄阳檀溪寺改制外国金铜佛顶髻的普遍认同[2],佛陀造像原本盛行的球状高肉髻始渐为呈馒首形的相对低缓的顶髻所取代。然缪宇墓所出铜坐像却无此种早期佛陀造像重要标志的高肉髻,而所谓“头发向后梳成一髻,上横插一簪”,则实为脑后之发髻。与作为佛陀造像典型特征的高肉髻全然风马牛不相及。至于该件铜坐像还有“后背露出双足,足底肉结高起”以及“(足底)高肉结……都显示佛教造像的特征”一段描述,将铜像中国传统的坐姿与来自异域的佛教造像生拉硬扯在一起,则不免让人有不知所云、匪夷所思之感。
再次,中国早期佛陀造像例皆身着通肩紧裹式袈裟,其衣纹自两肩向胸前下垂,然后平联过去,衣纹转折处呈“U”形皱,看起来近乎一重重向外扩展的垂鳞纹。按,此种佛装应即是由犍陀罗雕刻中常见的通肩右皱式装束发展而来,其成因则在于受到了中国传统的严格对称观念的影响[3]。而类此胸前呈左右对称“U”形皱、衣纹具有较浓郁犍陀罗风格的佛装,自佛教初传中国的汉末三国直至十六国、南北朝前期,一直十分流行。直至五世纪中叶,自以云冈第20窟露天大佛所著之袒右半披式佛装亦成为佛陀造像的常服,这才打破通肩紧裹式佛装“专宠”的格局。甚至是在汉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所谓褒衣博带式佛装全面兴起、且后起的袒右半披式佛装几已绝迹的时代,通肩紧裹式袈裟仍然占有—席之地,可见此种源自古代印度及中亚地区的佛装根深蒂固的影响。
而缪宇墓随葬铜坐像所着右衽交襟长衣,则为典型的传统汉式便装。此种典型的汉式装束即便在佛教高度汉化的南北朝后期以迄隋唐,亦未见著及佛身,仅于宋代起,始见服诸少量比丘、圣僧及罗汉、弟子造像中。可见,交襟长衣见诸于佛教造像,实乃佛教日趋世俗化的一种表现。因此,类似交襟长衣的服制早在佛教初传中国之际,即与佛像这一外来尊神结合在一起,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有意味的是,邳州当地的文物工作者还认为:“邳州东汉纪年墓葬(即缪宇墓)出土的鎏金铜佛造像与后赵石虎金铜佛造像(即建武四年像)基本相似,而时间至少要早180多年。”按,后赵建武四年(338年)佛造像所服正为通肩紧裹式袈裟(图二),其与缪字墓铜坐像的服制在外观上差之甚远,已备见前述。
佛像坐姿,历来不出三种:(1)结跏趺坐,即左足置于右大腿上,右足置左大腿上,亦称金刚跏趺坐;(2)半跏趺坐,即右足置于左大腿上,左足置右大腿下,是为最常见的佛像坐姿;(3)善跏趺坐,即双足下垂坐姿,又称倚坐,多见于弥勒造像。缪宇墓鎏金铜坐像所呈现的屈膝跣足跪坐状,为先秦以来汉民族地区各阶层人士的通行坐姿,但在历代佛教造像中却未尝一见。
综上所述,足证缪宇墓出土鎏金铜坐像并非佛陀造型。且由其身着右衽交襟长衣及屈膝跣足跪坐等传统华夏古俗,可以断言,该件铜坐像所表现的必为汉人固已有之的特定行为举止,与外来文化无涉。
缪宇墓出土鎏金铜坐像的姿态明显呈头部左倾且缩颈、同时耸动右肩向上拍出右掌的动感态势,显然与作施无畏印的佛陀不相类属。窃以为,缪宇墓鎏金铜坐像屈膝跪坐、举手欲拍的姿态,实即唐代之“拍弹”[4],是一种流行于汉唐、兼含说唱艺术的俳优表演,《南史·王昙首传》中述及南齐大司马王敬则所作类似举止则谓之“拍张”[5],至于被塑造为此种行为姿势的俳优铜像,在河北满城1号汉墓及甘肃灵台傅家沟西汉墓、广西西林西汉铜鼓墓中皆有出土(图三)。这些铜像的共同特点是:屈膝跪图三“拍张”姿势的俳优铜像
坐,扬掌欲拍,动感甚强。缪宇墓随葬鎏金铜坐像的情态与细部特征,正与之符合。有意味的是,作此拍弹或曰“拍张”举止的俳优表演,非为伶人专司其事,身份高贵的皇室贵族心血来潮,也会粉墨登场舞弄一番,如《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注引《魏略》云及:“太祖遣(邯郸)淳诣(曹)植。植初得淳甚喜,延人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迄,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段,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耶?’”[6]南齐时,大司马王敬则“奋臂拍张”事,性质亦同于此。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伴随着由南京博物院、南京艺术学院、日本龙谷大学三家共同发起的“佛教初传中国南方之路”研究的深入开展,中国学术界对早期佛饰制品和单尊造像的辨识及进一步考察研究亦日益彰显,陆续发表荐介了不少与早期佛教造型艺术有关的遗物。但由于此种研究尚属早期性研究,故学术上的疏陋在所难免,但将缪宇墓出土鎏金铜坐像这样造型特征极为显著且有出土先例可循的汉代俳优铜像指认为早期佛教造像的,则前所未闻,故特予析疑辨妄,庶免造成学术上的混乱。
注释:
[1]陈永清、张浩林:《邳州东汉纪年墓中出土鎏金铜佛遗像考略》,《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2]有关道安改治外国铜像事迹,详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襄阳檀溪寺“有外国铜像,形制古异,时众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髫形未称’,令弟子炉冶其髻,既而光焰焕炳,耀满一堂……安曰:‘像既灵异,不烦复治’。乃止”。中华书局1992年,第180页。
[3]李静杰:《早期金铜佛的谱系研究》,《考古》1995年第5期。
[4]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4608页。另可参见《杜阳杂编》卷下:“(李)可及善转喉舌,对至尊(指唐懿宗)弄媚眼,作头脑,连声作词,唱新声曲,须臾即百数方休。时京城不调少年相效,谓之拍弹。”
[5]据《南史·王昙首传》:“于是(王)敬则脱朝服,袒,以绛纠髫,奋臂拍张,叫动左右。”同书《王敬则传》亦谓之:“抚髀拍张,甚为儇捷。”中华书局1975年,第593、594页。
[6]陈寿:《三国志》裴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第6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