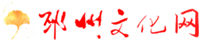谁也不否认,鲁迅先生是“怒目金刚”式的人物,“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嘛,他的文章像匕首,像投枪。其实,他是个有趣有情而又温暖的人,“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闲来读鲁迅,便读出了许多趣味。
我喜欢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照片,大气,儒雅,胸怀天下。我更喜欢鲁迅先生的大头照,就是带小胡子不苟言笑的那张。如果你仔细看,会看出那小胡子掩盖的嘴角,有一抹不易觉察的微笑,会心的、幽默的笑。
对于那些不着边际的批评家,他说:“厨子做菜,有人评他坏,他顾不得将厨刀铁斧交给批评家,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是啊,批评家都是眼高手低的家伙,不聒噪哪有饭吃?让他入厨,恐怕做一盘盐豆炒鸡蛋都比不上乡村妇女。鲁迅看不得虚伪,他这样说:“面具戴太久,就会长到脸上,再想揭下来,除非伤筋动骨扒皮。”因为虚伪像慢性中毒,渐渐浸润到虚伪者的五脏六腑。
我从先生的文字里看到了他的得意。因为他不轻易流露。这不流露,是一种暗自得意,一种玩的姿态,就像他讲话,逗的你捧腹大笑或忍俊不住,他自己是不笑的。
1936年先生病重,萧红去看他。他静躺在那里,不看书,不看报,不断看着身旁一幅小画。那画上是一个穿着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中奔跑着,在她旁边地上,还有一朵小小的红玫瑰花。这一幕好温暖!长裙子,飞散的头发,女子,风,奔跑,一朵小小玫瑰花。先生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生命的力量,有大欢喜。

你知道《野草》的温暖吗?进入《野草》纷繁复杂的世界,多么好的文字啊!可惜被大家忽略了。“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里,有许多蜜蜂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你看,颜色红、白、黄、绿、青,动有蜜蜂静有雪野,多么绚丽的一幅画!
先生是个极喜欢讲笑话的人。川岛新婚,他送了本书,扉页写道:“我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吧!”鲁迅先生的脸是一张不买账的脸,非常酷,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清苦,刚直,骨子里透着风流与俏皮,好像在说:怎么着,我就这样!他的脸非常配合他的文学,他的脾气,他的命运、地位和名声。
我初中就偷偷读鲁迅了。那是除了必读的浩然,鲁迅才是真正想读的书了。对他的杂文似懂非懂,再硬性安上“阶级性”就更感乏味。唯有他的散文和小说,读起来趣味而温暖。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家乡父亲的西瓜地里,月光如水,就想到了“闰土”,那晚没有蝴蝶和蜻蜓,当然也没有猹。那一刻,我与少年闰土合二为一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紫色圆脸,头戴小毡帽,项上套了一个银项圈,一双红活圆实的手。但我手中没有钢叉。我有些失望。而今,中年的我,是否也酷似老“闰土”?“身材增加了一倍,脸色灰黄,很深的皱纹,眼睛四周肿得通红,头戴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又粗又笨像是松树皮了。”我偷偷揽镜自照,发现除了那顶破毡帽,其余皆与老闰土吻合。幸也?运也?命也?中年的我,只留下一地稀碎的叹息。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活用了一次鲁迅,闹个不欢而散。我们都发福了,唯独一位杨姓女同学拼命减肥,五十了亭亭玉立地骨感。我善意地说:“你真像豆腐西施杨二嫂,细脚伶仃像个圆规!”杨同学生气了:“我老了,没有豆腐可以吃,但我绝对不像细脚伶仃的圆规!”人老了,就戾气十足不可爱了。
读了四十年鲁迅,常读常新,趣味十足。今生离不开他了。“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天涯过客。”我们都是过客,但鲁迅的书,是我行囊里的一件贴身棉布衫。